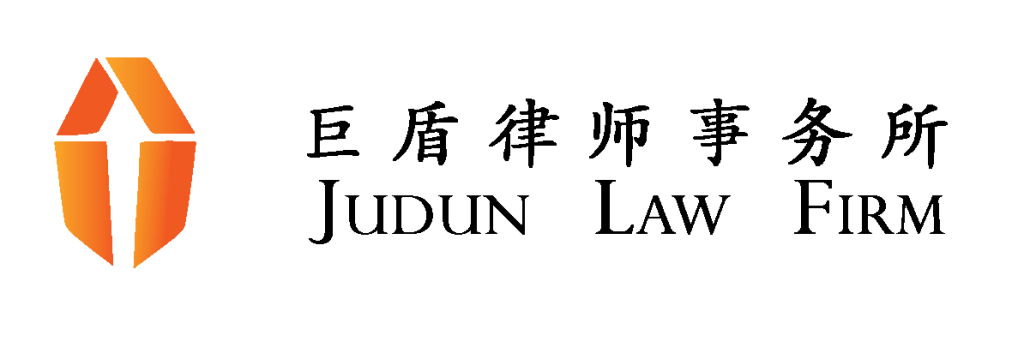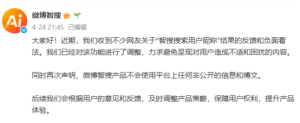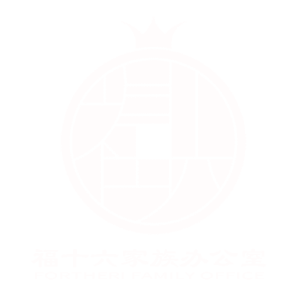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确立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的司法审查标准,明确不同类型案件的司法审查尺度,公平合理地保护和平衡股东、公司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现代公司制度,促进投资是解决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核心问题。
虽有上述规定,但实务界仍有观点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精神,诉讼时效抗辩是针对债权请求权的抗辩,客体为请求权,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对应的诉为给付之诉,但是确认之诉中提出的诉讼请求所对应的实体法上的权利并非请求权,而是形成权。虽然在名义上被称为请求权,但实质并非诉讼时效客体的请求权[1]。因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不应使用诉讼时效制度。例如,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鲁高法发〔2007〕3号)中认为,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不受《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的2年诉讼时效的限制
因此,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诉讼时效尚无统一的司法实践。从规定及司法指导性文件的时间沿革角度而言,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似乎逐渐倾向于不适用诉讼试时效规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截然相反的相关司法指导性文件均在有效期内,从防控诉讼风险的角度而言,股东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股东资格被侵犯之日起2年内提起诉讼,以避免可能存在的诉讼时效风险。
1)公司股东过半数同意或公司在实际出资人出资时即表示认可,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施恩初与江苏国美置业有限公司、王庆云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二审判决[(2015)苏商终字第00419号]即持该种观点,而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张炎康与南通汽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判决[(2015)通中商终字第00622号]中则明确即使能够证明实际出资,如无法取得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则无法显名。特别地,如公司章程对显名有更严格约定的,按照公司章程执行。
2)实际出资人实际参与了公司的管理或其他所有股东在实际出资人隐名投资之时就知晓并认可的,如江苏省宿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赵加建与宿迁市鑫嘉达置业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二审判决[(2015)宿中商终字第00257号]中认为,公司其他股东同意实际出资人参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使表决权、分红权等股东权利的,属于间接同意实际出资人显名;同时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黄德元与苏州华伦企业发展有限公司、陆勇军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判决[ (2014)苏中商终字第01176号]中认为,实际出资人外的其他股东与实际出资人签署《隐名股东投资协议书》,均知晓实际投资人隐名投资的事实,实际投资人要求确认股东资格不会破坏公司人合性。
但是,如果代持的是股份公司的股份,则确认股东资格时不需要获得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的认可,如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在刘爱萍与被告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股东名册记载纠纷案判决[(2014)玄商初字第1429号]中认为,股份公司强调资合性,公司法对出资人的主体并无过分限制,只要公司章程无特别约定,股东只要对公司履行实际出资义务,就能够成为公司股东。
因此,有限公司的股权代持与股份公司的股份代持适用不同的司法审查标准,有限公司更强调人合性,因此在确认股东资格时不仅要证明实际出资,存在代持合意,还需要取得公司其他股东半数同意(包括直接和间接)或特殊情况下取得公司的认可,如果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有特别约定的,仍需要个案分析;而如果代持的是股份公司的股份,如果公司章程对股份转让无特殊约定,则只需要证明已完成实际出资且存在代持合意即可。
在股权代持类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代持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实际投资人合法的投资行为是其获得股东资格的基础与前提,否则即使与名义股东存在真实的代持关系,仍不能取得股东资格。如最高人民法院在博智资本基金公司与鸿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欣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136号]中即持该种观点。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中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公司、其他股东或利益相关方能否起诉确认某股东(显名或隐名)不具有股东资格?这一问题具有其现实背景:一是实践中公司投资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情况是现实存在的,且属于股东争议中的频发纠纷;二是在股权交易有效性或履行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股权出让方虽属于名义上的股东,但受让方实际行使股东权利,出让方是否可以请求确认受让方不具有股东资格(股东资格否认)?
对于上述问题,有几个解答的思路:一是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属于积极之诉,而非消极之诉,即只能由股东或出资人请求确认自己具有股东资格,而不能请求否认股东资格,如最高人民法院在沈阳市东陵区南塔村民委员会与沈阳市浑南区市场开发服务中心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1092号]中即持该种观点;二是在公司投资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或抽逃出资的情况下,追究投资人的责任首先应当通过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来进行,如股东资格除名,而不应由法院直接作出判决,否则存在司法过渡干预公司内部管理的嫌疑,此种诉求超出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范畴,应通过侵权之诉获得救济。
实践中,对于未经招拍挂程序的国有股权处置或增资型国有股权设置[1]的效力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司法实践,肯定观点认为国有股权交易的招牌挂程序属于一般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法律规定,未经招拍挂程序交易国有股权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或增资扩股协议的法律效力;反对观点认为国有股权交易的招拍挂程序是国资管理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或增资扩股协议无效,如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沪二中民三(商)初字第81号民事判决书,认为:国有股权转让违反《产权转让办法》等相关国资监管的法律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未经评估和进场交易,擅自处置国有股权,交易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实际上,司法机关对这一问题的态度相当保守,甚至对于违反地方国资监管部门根据《国有资产法》及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规章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国有股权回购行为也认定为无效[2]。
因此,在确认股东资格纠纷案件中,如果涉案股权为国有股权,则除了关注是否实际履行出资义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或增资款)这一实质要件外,还应当特别关注国有股权招拍挂这一形式要件,如果不满足这一形式要件,则案件结果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14条的规定,外资股东拟确认股东资格时不仅需证明履行了实际出资义务,还需要取得外商主管部门的批准。但是未取得外商主管部门批准是否可以取得股东资格却存在不同的司法实践。如上海市(2008)浦民二(商)初字第2541号、(2009)沪一中民五(商)终字第7号判决中认为,外国人继承内资公司股权成为股东不改变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地,不导致公司的性质变更为外商投资公司,因此,该公司股东的变更无须外资审批机构的审批。而广东高院在潘某与张某等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判决[(2014)粤高法民四终字第48号]中则认为外商投资企业隐名股东请求确认其股东身份,诉讼期间未获得外商投资公司企业审批机关同意的,法院只能确认其实际出资人身份。上述两个案件虽然属于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件中的不同类型案件,有所差异,但是从外资股权管理的角度而言却是两个冲突的司法判例。
近年来,中国外资主管部门频繁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外资监管文件,建立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管理更加透明和可预期,因此外商投资更加容易。实际上,现阶段的外商投资已不同于较早的历史时期,审批的色彩已日益淡化。但是,从诉讼风险的角度而言,实际投资人(隐名股东)或受让取得外资股权时应当获得外商主管部门的批准/备案,以降低诉讼结果的不确定性。
因此,如果投资人投资入股时未取得金融监管机构的批准,则可能构成股东资格确认的实质性障碍。如陕西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上海天迪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西部信托有限公司、陕西天王兴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二审判决[(2010)陕民二终字第09号]中即认为,当事人不能以其意思自治而超越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未经信托公司主管机关批准前,投资者不能依据股权转让合同而当然取得信托公司的股东资格。
金融机构或类金融机构股东资格的前置审批程序是否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值得商榷,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投资者在投资入股金融或类金融机构前,须取得相应主管机关的审批,否则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股东以犯罪所得财产投资入股时,并不影响股东资格的取得。在刑事程序中,可以通过拍卖公司股权的方式追赃,保护受害人的权益。